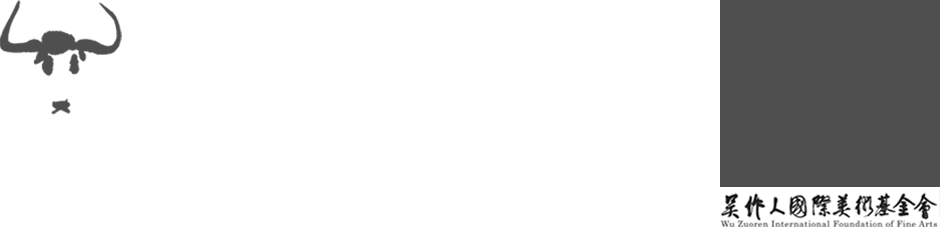吴作人的油画造诣及其风格变迁
艾中信
在30年代初,我国去比利时留学的青年中间,吴作人的学业成绩名列前茅。他在国外学习期间,深得弗拉曼画派的精萃,且在风景、静物画中灌注着中国绘画艺术的情致;回国以后,又注意于结合中国的实际和艺术传统,在油画技术上有所变化运用,其肖像、风景及静物等作品,显示出具有民族气质的特色。
1931年,吴作人考入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录取在该院院长巴思天教授的工作室学习。仅仅一年以后,他便在全院暑期大会考中以一幅油画男人体获得学院金质奖章和桂冠生称号,学院授予他个人画室,准许他个人使用模特,并提供所需物质条件。
他这幅得奖的人体习作,除了造型技术上达到了学院教学的规定,还应当看到它不按学院派的陈规,把技术运用得很活泼自由的一面。作画的时间,按学院规定有两星期,他只画了一星期,一气呵成。这幅画充分体现出他对人体基本练习的要求——严谨、简练、概括、感觉敏锐,技巧生动活泼,色彩透明、细润,很有弗拉曼传统的特色。从这个人体的胸腔部分、锯齿肌、腹肌等很不容易处理好的部位,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观察入微,手法敏捷,形体的细微末节都表现得很充分,但是一点也不感到累赘,形体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稍后,他在创作《纤夫》、《打铁趁铁热》等作品时,从这种技巧又进一步加以提炼,做到用笔省俭,但造型并不松散,因为他抓住了关键的结构要点。在这一点上,和他早年受到徐悲鸿的素描影响也有关。
作品的艺术价值,往往与艺术家自身的世界观、艺术观以及整个艺术修养紧密相联。当年中国留法学生筹组画会时,曾写信给吴作人征求意见,吴作人回信谈到了美术和社会的关系,提出“跟着社会而转移同时转移社会的”艺术观。他认为“艺术是入世的,是时代的,是可以理解的”,并指出“亲尝水之深,火之热”,“对于劳动者的歌颂,于贫困之同情以及人类反抗压迫,宁愿血肉牺牲而求自由解放之雏具的情绪,都成为现代艺人著心力之点。”他的油画创作,基本上是实践这个艺术观的。(见1934年2月号《艺风》)
吴作人在他的个人画室中完成了三幅创作——《纤夫》、《小组会》(表现一些生活在下层的工人开会的情景)、《打铁趁铁热》(表现打铁工人的劳动)。当时留学法、比、英、德等国的美术青年,很少画主题性创作的,画劳动题材、社会生活的更是少见。无论中国的留学生,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或比利时学生,对这样的创作都不重视,因为它卖不了钱,展览会征集作品时也不受欢迎。只有一两个思想比较进步的意大利、阿根廷同学,说他是无神论者,因为他的创作表现了人的劳动,提出了社会问题,不是神,而是人自己在掌握自己的命运。
吴作人的油画技法,也有抒情写意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巴思天晚年画风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受了中国水墨画技巧的影响。这种技巧很讲究笔意的起承转合,前笔和后笔的融接,达到整体感的高度完整,浑然天成,别有一种笔法松动的风趣,开辟了油画表现的新意境。这种油画的意趣,如果要在欧洲寻找前驱者的话,可以提出戈雅、德拉克洛瓦、蒙卡契和马内等。
吴作人的油画造诣,在静物画上,可以鲜明地看到通过巴思天接受了弗拉曼画派造物精微的特点。不过,吴作人的静物格调比弗拉曼一般追求逼真的水平为高。北欧静物确实描绘得很精细,其状物之真,可称能品,但缺乏超乎自然生态的灵气,也就是画家、欣赏家心目中那种不拘于实物本身的胸中逸气。花卉、器皿、鲜果以及鱼肉之类,之所以成为一种绘画题材,静物画之所以成为油画的一种体裁,决不在于画家笔下状物的逼真,而贵在有艺术的概括、提炼,它和人物、风景画一样,也要体现一定的意象。这种静物的形象化境界,有时比风景还难以把握,因为这些对象往往是极其平常的东西。吴作人一向不以为逼真就是艺术,虽然艺术必须求其真,艺术家的眼光如果做不到见常人所未见,发常人所不发,那末,极平常的半棵卷心菜、一块面包、一片鲜鱼,就很难给人留下艺术的美感,甚至反而使人腻味。在这里,传神写意的技巧,通过他的油画笔法、刀法,摆脱了物象的约束,超过如实的形似,达到了形神的结合,使人看了感到比真的还真——进入艺术境界的真。吴作人的油画造诣,得益于静物画的地方很多。他很喜欢画迎春、芍药、月季等花卉,取其清新、秀丽,富于生气。他也喜欢画各种质地的器皿、甲胄,探索无机物质的生命,术如点石成金,多画静物对磨炼油画语言也是有效途径。
吴作人回国的第二年,1936年,先后创作了《出窑》、《湖上风云》;在抗战期间,他画了《播种》、《毁灭不了的生命》、《空袭下的母亲》、《赴战的前夕》以及《黄帝战蚩尤》画稿。此外,他还画了我国古代大医师华佗为关云长刮骨疗毒,这是很少有人接触过的很有意义的题材。
在回国以后的创作实践中,他逐渐感到弗拉曼的油画风貌不能适应国情,首先发觉到弗拉曼的明暗和色彩运用是北欧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反映。地理环境势必影响人们的欣赏习惯,久而久之,就形成地区民族的审美爱好。他到青藏高原以后,对这个问题感触更深,他的油画风貌,也就随之有所转变。但是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画家的心境和思想情绪,使他的画风在40年代变得宽旷,到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而趋于豁达。
吴作人的作品以抒情见长,他的真率的感情抒发,表现在1936年的风景画《湖上风云》上,是黯然肃杀;在1943年的《沙漠神水》上,则转而为苍茫落寞。40年代初,画家不堪重庆的窒息,只身遨游青藏高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月里,画家身处边陲,心情是沉重而又激越的。
1945年创作的《藏女负水》则相当清明,在他的油画上,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蓝天白云和明丽的阳光,一湾溪流,滋滋淙淙的,他幻想出一幅沁心的和平景象。这是他接触到高原人民生活和敦煌石窟艺术以后的一个鲜明的风格转变。应当指出,这和他开始致力于水彩画和水墨画也是分不开的。
吴作人油画风格的鲜明转变是在建国以后,50年代,他迈开健壮的步伐游历祖国各地,登山越岭,体验生活,朝气蓬勃的建设事业和美丽繁茂的自然风光,都成为画家尽情抒写的称心题材。他创作了《佛子岭水库》、《草原云雨》、《镜泊飞瀑》等许多风景画,反映了心情的愉悦。其中《三门峡》是一件富有民族气派的主题性风景,是他计划创作《黄河三部曲》中的第一幅。它描绘了滚滚洪水,走笔连绵,非但不为复杂的现象所窘迫,反倒在绰约潇洒的技巧中,显示出惊涛汹涌,沙流宛转,如闻冰崖喧豗之声,如见回旋沉浮之势,这是画家对景物有悉心的体察,对笔墨技巧作了切实推敲的结果。
与画风有着密切关系的描绘技巧,对作品的艺术素质起着重要的作用。吴作人的抒情风格,在具体的表现上,必须归结到他的绘画技巧的抒情性。他喜欢用刀作画,人物的服饰、静物、风景,用刀的地方很多,刀法的多变和熟练驾驭,是他的油画语言丰富多彩、词藻优美的一个因素。《哈萨克人》上的皮靴,《静物》上的炸干鱼和紫色卷心菜等,都是在用笔的基础上,再用不同的刀法来完成其艺术表现的。用笔赋色,用刀勾划的方法,在《三门峡》的黄河水流上达到了出色的效果。近处的黄水旋涡,远处的长流,洋洋洒洒,都是从刀尖上宣泄出来的。他之所以喜欢在这些地方用刀来表现,并不是故弄玄虚,哗众取宠,而只是为了更好地把对象画得更充实,更生动,更有感染力;对吴作人来说,非如此不足以宣泄他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和水势的造型又是结合得那末紧密。离开了这个目的,徒事笔墨的玩弄,只能把形象表面化,简单化,艺术上也就沦为浅薄。看了吴作人在《三门峡》一幅上的油画技巧,可以领会到一个画家的艺术风格的臻于成熟——思想感情、艺术修养、绘画技巧的熔为一炉。这就是吴作人的油画风格,这种风格,在他的另一些风景画,如《镜泊飞瀑》、《大连海滨》中,也同样地体现出来。
吴作人在50年代画过许多肖像画,其中可以油画《齐白石像》为代表作。此时,吴作人在人物塑造上攀登到了一个新高度,油画的风格更具个人特色,而且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又有所突进。
肖像画的创作构思是很多样的。不借助于和人物的身份、职业必然相联系的环境、道具、服饰的陪衬,而专注于人物形象的刻划者,可以说是肖像画的基本一格,而且是比较难于做好的。没有复杂的情节构思,甚至没有任何情节,无须博引旁征,似乎容易些,但是这种肖像画要求在创作上具有较高的艺术概括力,使主题思想寓于默默然的人物形象之中,其实是难的。
吴作人所作的《齐白石像》,把一代画师齐白石老人的堂堂气度和奕奕神采,表现得妥帖、中肯,恰如其分。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就,最重要之点在于作者对老画家有着透彻的了解,在精神上臻于要沟通的结果。人物形象的每个部分,大至身躯,细至须发,其造型设色,无不与气度神采有关。《齐白石像》敦厚庄重,泰然自若,这一安详的仪态已奠定了人物的造型基础。设色的基调,是虾青大袍与白发童颜之相映,显出老人阅历之深,而又具有赤子之心。若论细节,可以举这幅肖像所以经看的眼神、嘴神、手神为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不待细述。嘴神、手神在《齐白石像》上,实有独到之处。从老画家久经锻炼的双手,可以见到劳动生活的烙印,而那职业性的习惯动作——右手握笔的姿态和隐现在银髭下作吮笔状的嘴神,实不下于凝神而思的传神阿堵。这种小动作的神态,在被画者是出之无意,在作画者则出之有意无意之间,而在读画者则深为惬意。从形象的整体来看,这只能是若隐若现的细节,过事渲染,不免矫揉造作,处理得当,则能恬然生色。服从大局的细节描绘,足以引人入胜,耐人寻味,使读者得到欣赏的满足。
当时,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馆长美术鉴赏家札莫希金在看了《齐白石像》说,这件作品可以和列宾的《托尔斯泰像》匹配。这一评论很中肯的。论油画语言,确实有许多共同之点,但人物的气度很不相同,他们之间有东方西方之别。马克西莫夫和博巴对《齐白石像》和《三门峡》都有类似的评论,说这些油画是从中国人的眼光来观察的,像中国画一样,单纯,富有诗意。外国油画家的看法可能客观些,我们中国的油画家则有这样的感受,觉得吴作人从精通弗拉曼油画逐步演变到现在的风貌,他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走着自己的路子。
在油画民族化方面,表现在技术、技巧上,《齐白石像》也有许多值得探讨的东西。在构图的规律中,绘画布局的根本法则是黑白的总体设计,这是中西共通的原则,而中国的水墨画最讲究大块黑白的布局处理,因为在水墨画上,色彩一般不占重要的位置。基本上以素描为手段的版画、插图则讲究黑、白、灰,现在的油画也很注意这个三大调的装饰效果。吴作人的水墨画上信守‘知白守黑’的原理,在油画上也运用得很得体。齐白石头上的那顶乌绒软帽,它覆在老人脑门上,产生恬适之感;它和多少有点夸张的宽袍大袖配合起来,是纯属中国型的。同时,大块的黑色、青色,给画面上压上一定的份量,用来衬托明晰的脸色,这是‘知白守黑’在油画上的妙用;和背景的灰色调恰好形成稳重而又空灵的素描总体结构,这幅画采用平光,不强调明暗对比,减弱阴影,但未尝违背写实的明暗法,这也是从‘知白守黑’的基本原则出发的变化运用。
在笔法技巧方面,最明显的是用破笔画银髯,疏落有致,是油画,又有毛笔的神韵,那眉毛又是在扑好的底色上用秃笔‘拔’出来的。这种笔法,只有在深入体味造化以后,在精通油画性能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为了照顾老人的体力,在创作《齐白石像》的过程中,只对着老人画了一次,在安排好大局的构图上,一气呵成了最主要的脸面和双手。但是总的说来,吴作人的作画习惯是,作好充分准备,一鼓作气,攫取形象,以求得最大程度的艺术生动性。衣服是请别人穿着画的,红色沙发是参照一片织锦设想着画的,从以上情况,也可以看到他艺术方法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