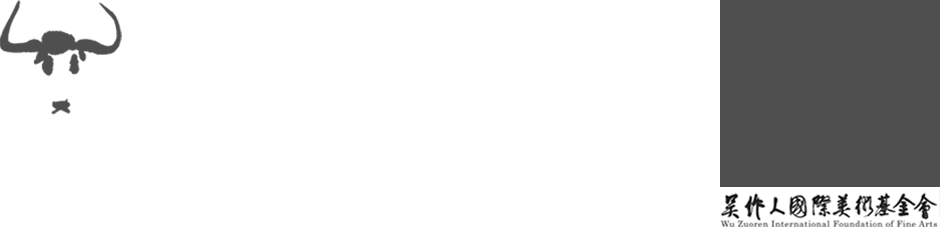文/韩见
去年12月17日至今年2月20日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举办的“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专题展,共展出76位女性艺术家的150余件作品,既有狭义的画家以自己为摹写对象的自画像,也有广义的、蕴含艺术家自我叙述意向的作品,包括绘画、雕塑和部分综合材料作品。

一个能够同时刺激普通女性观众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者神经的主题——“女性自我画像”。策展人姚玳玫这样解释她的思路:“采用历史研究、图像研究和女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把自画像作为一个角度,来检视一个世纪女性艺术家自我命名、自我摹写、自我表达的历程,一种女性精神存在的历程。”通常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批评在这里并非主角,展览以中国女性艺术从诞生、走向成熟到自我身份转换、媒材更新的全过程为轴所呈现的,是一种开放、交错的叙述。
去年12月17日至今年2月20日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举办的“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专题展,共展出76位女性艺术家的150余件作品。展览分为“上篇:民国时期”和“下篇:共和国 60年的女性画像”。其中民国时期女性艺术家作品,数量虽然不多,却表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和不俗的感染力。姚玳玫介绍说,民国时期女艺术家保留下来的“自画像”作品不会超过10幅。“从民国至五六十年代,女性艺术家实际上在我们整个艺术的主潮流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没有多少人注意她们,她们也很安静,自己做自己的事,在公共空间也没有留下多少东西,是一群失踪者。”然而这些第一代接受现代美术科班教育的女艺术家,恰又是中国现代女性美术的开荒者,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新时代女性美术的走向。有意思的是,1929年4月国民政府第一届全国美展上,女性艺术家中的佼佼者潘玉良、蔡威廉、王静远等,都以自画像/肖像画和人物雕刻备受称赞。在解除女禁不久的中国,个人主义思潮广泛传播,画人物或画自己对于女性绘画者来说是一件别具意味的事情,经由西方艺术的形式,她们得以探索自身、确立自我。她们的表达未必是批判性的,更多是情感性的。这条艺术线索不仅由她们自己在此后的创作生涯中延续,而且也被后来的女性艺术家继承和发扬,即便在“个人主义”被根除的50-70年代,女艺术家的自我形象依然隐藏在各类女性形象之中,这可能与女性倾向于通过认识自身来认识外界的认知方式有关。
在共同的主题之下,民国时期的女性艺术家们的“自画像”展现出丰富多样的风格。潘玉良的《窗前的女人体》,人物浑厚舒张,在空间构图上受到塞尚的影响;萧淑芳的《小妹》用深沉的邻近色传达出朴实、宁静的性情;邱堤的《布娃娃》似乎隐含着少女的孤独与偏执;关紫兰的《少女》如她本人一般清丽饱满,陈丹青曾评价该画“令人眼前一亮”,使并列的其他作品失色。尤其在为大众所熟知的传奇女画家潘玉良丰富而坚实的色粉画中,性别意识和自我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追溯她的个人经历,确能感受到其画作与她的生命体验气息相连。除了在展览中展出的两幅广义的“自画像”,潘玉良在不同时期还画有多幅《自画像》,更为直接地表述她个人的生命轨迹。本次展览总策划朱青山这样总结自画像的艺术性——“这种艺术性让每一个独立的女性,不再以女性的集体身份出现,不再受任何传统意义或现代意义上的‘妇道’观念的局限,而是在被张扬和掩饰的个性之下,完成她的自我理想虚幻实现的仪式。”
从整体上看,90年来女性画笔下的个人境遇同时显现为一种历史的证据,这在展览下篇以社会状态为依据划分的4个部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从50-70年代的“铁姑娘”形象,到八九十年代“自我”的抬头,直至新千年以后女性的自我画像从感性的“经验”表达走向理性的、观念的“超验”表达,时代的脉络清晰可见。对此,姚玳玫表示:“我在考察女性自画像的过程时就发现,自画像从‘个人’切入,但最终出来的,却可能带有‘时代’的痕迹。只要你把图像阶段性地放在一起,你就看到图像背后时代对个人的制约。在个人化的时期也无法逃脱这种制约。”一般而言男性化的“历史”与“时代”,被女性的形象和思绪挤压到细微之处、以女性自我的形式曲折地表述出来,也正是这个展览可堪玩味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