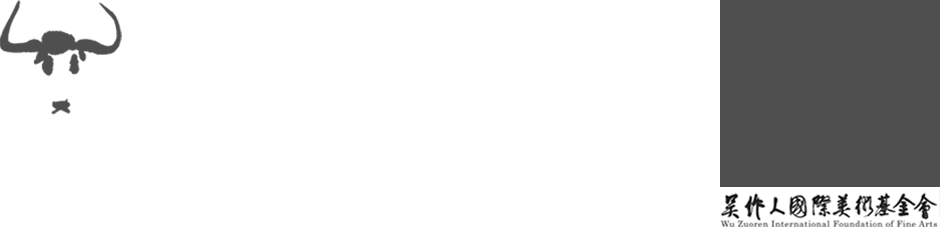含蓄深厚之美
——吴作人的水墨画
钱绍武
听说吴先生的水墨画起始于40年代青、藏行旅之中。并非刻意而为,因此往往即景生情,随手拈来。自此,他觉得以传统笔墨写意抒怀,更能表达其审美情感,遂逐渐从油画转向水墨。到50年代,有“十张纸斋”之兴,好友相聚其家中,从论艺短长,又用各种工具进行速写,相嘘以湿,相濡以沫,既是适性怡情,又收切磋之功。吴先生在晚画会上常用羊毫勾勒人物,锻炼造型,并坚持晨课书法,钻研传统笔墨。他的中国画由是发轫。高原的牦牛群、戈壁沙漠的骆驼队,大概是时萦梦寐、难以忘怀的吧。骆驼的沉着稳重,牦牛的雄放活泼,几道横线,数堆沙丘,简约明净而意趣自足,但这些杰作往往被藏之箧笥,随意置之,二三好友之外,不为人知,世人所知者,熊猫、金鱼而已。但积之既久,自会不胫而走,且因兴之所至,以至所涉日广;立足千年的雄鹰是吴先生有感于当时人民的奋发精神而作,意境之高旷,造型之奇特,大概只有“横空出世”四字足以当之。熊猫总是逗人喜爱的,但吴先生画熊猫,不过寥寥数笔,不着形相,只是传达了憨厚天真的意态,令人如赏婴戏。若是惟恐不像又着意刻划,则往往失之于实反而意趣索然令人望而生畏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了吴先生“游于象外,得乎环中”的艺术修养之功。吴先生画的是“意境”,而不是“实况”,这方是中国艺术的真谛。飞翔的鹤,则体现了另一种境界,寥廓高旷,令人神往,真是“晴空一鹤排云上,遍引诗情到碧霄”。而我最喜欢的是黑天鹅,潇洒蕴藉而气度高华,优游而风神超脱,可说发挥了笔墨的极致,最理想的水墨题材竟未为历来画家所发现,而吴先生中有所感,外有所遇,得之于心,挥之于纸,人格画格融而为一,真是天造地设,得未曾有,这是中国新文人画的发展,最根本的特色是“意境”超妙。
吴先生的画有着中国哲学的深厚底子。他经常教导我们,作画必先立“意”。这立意,决不是简单的首先“确定主题思想”之谓,而应着力于“意象”的创造,是画“心中所想”,但这心中所想的又决非无本之木主观自生的东西,而是“仗境方生”,是由作者在生活实践中触景生情而来。而归根结蒂,还是我们传统的思维方法所决定的,我们的哲学思维方法,是“体验派”,我们哲学的基本倾向是阐述哲学家自己对万事万物的“体验”和“心得”,而不是去分析客观世界本身。分析客观世界本身恰是欧洲哲学家的基本倾向,因此人们称他们为“分析派”。吴先生的画正是反映了“体验派”的根本倾向,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就着意于画我们自己对万事万物的“体会”、着意于抒写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所产生的“兴会”和“意趣”,而不是去斤斤于刻划客观生活本身。正因如此,我们就摆脱了模仿现实的枷锁,赢得了随意抒写的自由。但是,我们又尊重决定我们情感的生活实践和客观现实。所以我们写实而不拘泥,写心而不杜撰。正因为我们能紧紧抓住自己“体会”的核心,而不是描摹繁复的客观世界,所以我们才能单刀直入,一针见血,才能要言不繁,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举要治繁。吴先生水墨画之一大特色是含蓄深厚之美,这是值得我们深想的。
我认为吴先生水墨画的含蓄深厚之美还来自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渊源,我称之为“玉文化”。大概自石器时代的晚期,我们就很重视玉,玉不仅是装饰品,而且代表了一种崇高,一种道德观念,几乎贯穿到各个方面。人们为了表示友谊的永恒,往往赠送玉环、玉佩。皇帝要启奏上天,把发言提纲书之于玉圭,举行盛典要用金镶玉的仪仗。这玉,为什么受到如此重视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外表十分温润,而内部却无比坚刚。这种原则后来竟贯穿到一切方面,我们的武术讲究“太极拳”,强调内功,外表看来软绵绵,而反击之力强大无比;我们的中医,主张治本重于治表;书法讲究“屋漏痕”,也就是主张要力透纸背而起讫无端,不露锋芒。为人也是如此,对锋芒毕露之辈往往看不大起,而讲究“真人不露相”,讲究外柔内刚。一言以蔽之曰“含蓄”’。在吴先生的笔下,一切暴戾霸悍之气都化为深厚含蓄之美,烈酒都成了老窖,温文尔雅但决不是软弱轻飘,亲切动人而决不是讨好迎合,令人相看不厌,如啖青果。
看了这些水墨画不禁令人想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少中国的老一辈油画家好像先后都画了不少中国画。悲鸿先生、作人先生、风眠先生、希文先生都是如此。他们都深入地研究了欧洲的油画传统,即以欧洲传统而言,他们当时都已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引进”。他们在融化、吸收了以后,很快产生了自己的面貌。推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我们先已有着很深的艺术传统和很高的艺术水平,所以越深入学习外国,多所比较之后,越发体会到我们自己传统的特色,和我们自己民族传统的可贵之处,最后就自然而然地致力于把中外精粹熔于一炉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以我个人极肤浅的爱好而言,我十分尊重悲鸿师的油画成就,但是更喜欢他的中国画;我也喜欢吴冠中先生油画,但越来越喜欢他的水墨画,觉得亲切自然,简要入神。对作人先生的画,我的倾向性的确是没有那么明显,因为作人先生的油画早年是如此深沉,中年又如此明朗洒脱,总的特点是开阔大方,精要凝重,在中国而言,则迄今为止,不可逾越。但站在吴作人先生的水墨画前,却是又一种心情。如果说在他的油画前心里不禁高呼“大师”,为磅礴的气势所震撼,那么,看了他的水墨画却如对挚友,只觉妙趣横生,可以忘忧。温厚典雅如赏古玉,清新舒畅如对小溪。似乎一点一划都直接自内心流出。我总觉得中国的笔墨更能直接体现作者的心态。清代的王石谷说士大夫与俗工的区别全在一“写”字。这“写”,既要“再现”,又要“表现”,既是客观的高度概括,又是主观的充分抒发。这种“写”的原则在欧洲绘画中,似乎在十九世纪以前还只是大师们不自觉的自然流露,还未成为被有意识运用的一种艺术语言,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为少数画家所采用。而成为普遍重视的原则,则是二十世纪后的事了。但这时的“写”却又过分重视主观抒发,过分不重视客观规律,走向了另一极端。而作人先生深深懂得中国画的精粹,也深知中国哲学的要义。我们从不走极端,我们的原则一直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透澈掌握造型规律基础上充分发挥书法艺术抒写心态的特长,既能挥洒自如,又能下笔有由,真是闻一多先生所说的带着镣铐的舞蹈。这才是任何大师的最高境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不是欺师灭祖的“野狐禅”。
我觉得吴先生的水墨画最充分地体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全部精神内涵,体现了中国儒学哲学的优秀精神,温柔敦厚而又坚贞不屈。
以上,也就算作是我学习吴先生水墨画的一点体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