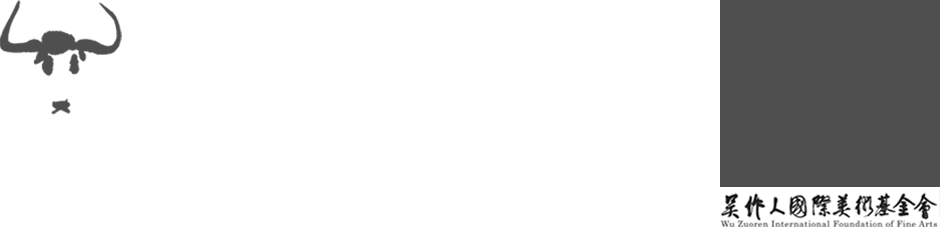在吴作人的艺术经历中,一共有过三次“晚画会”。
一曰“曾家岩晚画会”,1940年于吴作人在抗战陪都重庆之住所举行,基本上是几位青年美术家专为吴作人安排的一项“康复疗养活动”,其时,吴作人在战火中新逢丧妻(李娜)失子之人伦惨变,又因过度悲伤罹患眼疾。曾家岩晚画会使吴作人很快振作起来,原本有可能开“战时文艺之新风气”,无奈,晚画会因战火毁家而起,又因战火毁家而终。国运如此,夫复何言。
二曰“洋溢胡同晚画会”,1946至1947年于北平宋步云寓所举行,冠以“中国美术学院画室”之名。时值山河光复,“全局之胜,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艺专复员开学,安置不少教员在洋溢胡同居住,晚画会在同仁切磋技艺之余也自然成为诸位芳邻的闲时小聚,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无奈,好景不长,因吴作人与执政当局失和,远避英伦,晚画会顿失砥柱,草草收场。
三曰“水磨胡同晚画会”(“十张纸斋”),1953至1957年于北京水磨胡同49号吴作人与萧淑芳的住所举行。新朝气象,国祚日隆,天下太平。一时间,水磨胡同人文荟萃,晚画会集素描、油画、水彩、水墨各专业之海内高手,更有文化艺术界各路名流趋之若鹜,“文艺复兴”,于斯为盛。水磨胡同晚画会所被赋予之意义,也早已超越美术和文艺本身,成为“政通人和”的典范。无奈,盛极而衰,与“苏式美术”一统江湖正相反,“十张纸斋”门外车马渐稀,败象渐露,至“反右”风暴骤起,遂告寿终正寝,迄今五十年矣。
纵观三次晚画会,与纯系“无组织,无纪律”的曾家岩不同,自洋溢胡同起,因发轫于国立艺专体系之内,始得到徐悲鸿的重视,赞许,乃至支持,为实践徐氏“提倡写实,学好素描,打好基础”的理想园地,吴作人不见容于旧政权而出洋韬晦,亦为徐氏刻意保全之功。“十张纸斋”则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竖起了“实践悲鸿主张”的大旗。
然而,有史以来,恐怕素描引起的争论从未如此复杂和尖锐——它原是基本功,但被“形而上”之后,就成了不学它便根本不配学艺术;可是学好了素描,表现人还是表现自然又成了问题;待至“苏式素描”泰山压顶之时,“全因素”和“提炼取舍”的观念又将“素描论者”割裂为不同的阵营;还有,千万不能忘记,管它哪种素描,和中国画之间的“别扭”,从头到尾,贯穿始终……
三次晚画会,三次无奈
吴先生,我们的“十张纸斋主人”,及其“‘和而不同’的同志”,关于“民族化的油画”和“推陈出新的国画”,做到了一代人所能做到的一切,也付出了一代人所能付出的一切;他们不能抗拒三千年以来的党同伐异之风,也解脱不了“秋风中第一片落叶”的宿命,所谓“家国共命运”之说,可以解嘲。
“十张纸斋”作为“一首余音绕梁的小夜曲”,曾经并且仍然以“和而不同”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激发起人们心中最深沉的回响。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十张纸斋(1953—1957)——中国现代艺术史的个案》总撰稿人
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