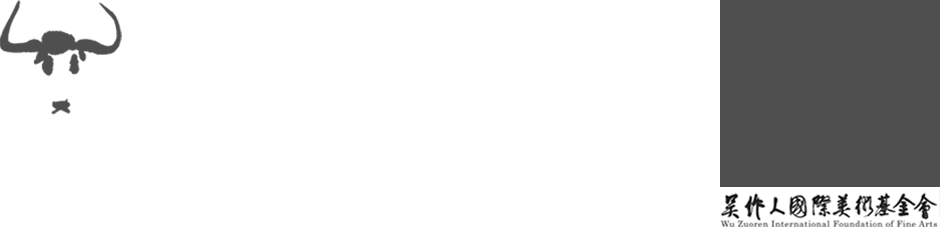美术学院的历史与问题
引言
朱青生
美术学院的历史与问题是艺术发展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自学院制度创立以来,艺术观念的变迁、风格的建立和延续大多在美术学院中展开。同时,艺术家又要摆脱和挑战学院体制对创作本身的束缚。因此,有必要考察学院制度及其代表的艺术经典的传承方式对艺术家的天赋和创造力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学院的历史渊源有二个:一是希腊古典时期的雅典,二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古希腊的学院是学者和艺术家集会和授徒的组织,将人对世界的掌握和解释作为活动内容,以科学和理性为基本观念和宗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将艺术从手工劳动上升到一种人文科学,因此设立了美术学院,以区别于行会授徒模式。在美术学院中,观察和再现形象(现象)世界的原则和方法逐渐完善,与透视学、解剖学,以及光学和力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并与化学、天文、地理及心理学(七艺)等学科相关,再与人形象和现象对世界的形相学的遗产和历史相关联。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艺术作为美术史的经典,构成了“美术”作为一门学科的判断标准。“美术”作为一门科学,其本质与其他学科接近甚至等同,美术学院即以此教授学生。当代的美术学院依然担负着传承与创新的任务,但却遇到了自身的问题。
美术学院的问题有二种:一种源自艺术与科学的差异,另一种源自传统艺术及其传授方法与现代艺术(实验艺术、先锋派和“当代艺术”)及其对艺术家的要求之间的差异。
科学和艺术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但二者分属人性的不同方面,经由人的不同的精神系统和生理感官作用于世界与生活,因此,历史上的艺术和科学虽然多有交错,互相促进,但它们是两回事!否则一种早已被另一种替代和吞并。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理想是把艺术提升为科学,并不是他们不明了科学和艺术的不同,而是当时艺术和科学的概念和现代不同。当时艺术的主要目标是探究世界,并用图画、雕刻或其他方式表述人对世界的认识。艺术成为认识世界、表现世界的途径,与科学的目标类似,这虽然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特色,追其源,还是受致希腊文化对艺术的定义和规范。
希腊艺术最根本的理念是理性和尺度。从表面形式上观察,希腊艺术的规则直接引自埃及,但是和埃及高度规程化和样式化的艺术相比,希腊的变革极为重要。简单来说,埃及的规则基于对一种规范的信仰,信仰基于人对于世界和人类的意识形态,由法老和僧侣——政治和精神统治者用国家制度和教义来强制推行。埃及虽有以手指等为单位的度量规范,但这种规范是用教义命名和规定的,一旦确定,就成为一种文化权威,用之衡量世界上的事物和设计人类社会的制度,而且延伸到对死后世界的统辖。埃及的艺术成为信仰和思想的载体,是人性中思想性的变现。导源于统治集团和统治传统的集体动机,指向社会和个人必须服从的目标,这个目标永远是超越和神圣的,而且同时是神秘的,不可证明,也不允许追问。不难理解,当埃及的政治和宗教权力发生重大冲突时(如十八王朝埃赫那吞时代),艺术样式的变更和表现方法的变化成为最为明显的特征。希腊人同样使用埃及尺度规范来制作艺术,但却是经过人为的测量和计算做成标准人体(Kanon, Canon)。如传世的波利克里特(Polyklet)的作品和吕希普斯(Lysippos)的作品,并不是教义或政治权力的需要,而是作为个人的艺术家,运用自己的理性对物质世界的中心形象——人体进行测量并经过计算得出来的结果。无论如何解释“美术”之类的概念,埃及人和希腊人同样是用尺度和比例来建造和表达“完美”或“理想”的存在,但这两种尺度却完全来自于不同的人性方面,具备根本的差异。也就是说,希腊尺度是理性的结果,它相当于科学,而埃及尺度相当于教义。因此,学院就在这种精神状态或人性特质上建造起来。令人不可或忘的是,雅典学院的门上,柏拉图写下的院规“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几何”的希腊词源就是测量土地,这种算计性正是理性的特质,也是科学的本质。在古希腊传统中,学院就是科学产生和传授之所在。
学院的科学性质的根源清理之后。对于艺术是否可以在学院被传授的问题,美术学院内部产生了疑问。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在《美术学院的历史》一书中梳理了史实。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所在意。他拜托沈宝基先生(1934年在法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1946年起与吴作人在北平艺专同事)译出了《美术能传授吗?》一书,书中提到:
艺术不可以被教授
艺术上“非理性的”观念,这一回轮到它进入教学中来了;它替代了一向作为整个教学学说基础的理性的观念。“非理性论”,我们看见它的出现,在十八世纪中叶还是犹豫,还是不定的,后来在十九世纪过程中,越来越明确坚定了。对于非理性论来说是独尊天赋,是浪漫主义;
对浪漫主义者来说,想象和敏感不能受理性的约束,学业的限制。艺术品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创作,而且像自然一样,不可从属于任何规则,任何科学;而只是由它的新颖,独立存在。不是什么选择问题,美丑问题,艺术家只能听从自己的灵感。天才无耐心。
引自[法]保尔·朗多斯基(Paul Landowski)著:《美术能传授吗?》(Peut-on Enseigner Les Beaux-Arts?)沈琪译
上文也给出了形成这种疑问的观念原因,即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艺术观念的冲突,其更为基本的原因是艺术与科学的差别。以科学性质(理性)为主导的作品,艺术上强调规律、准则、范式与和谐,以表现物质世界的现象和现象之上的“形而上”理想典范为最高目标,从而偏向古典主义;以艺术性质(情性)为主导的作品,艺术上强调自在、偶然、个性与激情,以表达人的精神为最高目标,从而偏向浪漫主义。人的本性的二个方面(理性和情性)本来与人的第三本性(思性)三性一身,并存于个人之中,并存于人口学意义上的民族和文化之中,并存于人类之中。无论偏重哪一方面,都可以并存不悖,相安无事。但是由于人的第三本性是信仰、思想及其外在意识形态所依据的思想性,它既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由本性的原因,同时又是人间群组各自认同、党同伐异、引发最根本冲突的根源,这种冲突与集团利益冲突共同形成了文化的差异、国家和民族的区隔以及不同的艺术观。也就是说,本来古典主义所说的“艺术”与浪漫主义论的“艺术”不是同一件事情,它们却要在学院里面争占创作阵地和权力、抢夺教席以申张自我的主张,教导学生。而美术学院本来是以偏向理性和科学的艺术观念为基础建造的,是古典主义艺术的基地,也是专门教授经典艺术的机构。但是当艺术家和思想家发现或者觉悟到艺术的本质并非仅仅如此,或者根本不是如此,问题就产生了。
第二个问题即美术学院教学与当代艺术实践之间的差异,其中实际包含着双重矛盾。第一重矛盾还是艺术和科学的矛盾,最后把艺术中的不可规范的因素当代化,从而继续着学院内部的争论,似乎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冲突的现代化。或者说,科学和艺术在美术学院问题的冲突,已经延伸进入了新媒体、新门类、新方法的教学领域,进入了设计、影视和计算机艺术、新兴综合媒体的艺术时代。第二重矛盾更为深刻。现代艺术运动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进行了四次重大的艺术观念革命,现在我们所说的“当代艺术”中的“艺术”,既不是古典主义的“艺术”,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艺术”,而是一种美术学院史上从未遭遇、处理和研究过新的人类精神领域。“艺术”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对个人的生活、心理乃至文化境遇和流行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Peter Schneemann提交给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中有如下表述:
在那些读起来好像英雄史诗一般的早期现代艺术史中,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必然在抗争着学院式的、官方化的艺术训练系统,而学院里的老师则多半不仅不支持他的艺术探索,反而对他进行打压。这位艺术家于是被迫成为一名自学成才者。因此,是艰难复杂的生活经历而非学院训练,造就了这位艺术家的辉煌。对20世纪的艺术学生们而言,一种位于内心召唤和职业选择的两级之间的、对艺术家身份的自我认同,较之建立在抽象信条、严格原则以及系统训练基础上的学院教育,无疑更具有决定意义。
面对面的、精准的指示,强制性的模式,以及关于风格的限制,这些现在都被一种自由的观念和一种伦理的维度所取代。通过艺术自我在艺术上的真实反映,艺术以新的方式被赋予了合法性。
在巴黎这个传统美术学院的核心基地,事情的发展更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特征。Dufrene教授的论文是这样描述的:
巴黎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艺术之都。如果说直到今天仍然有众多年轻艺术家到此求学,原因就在巴黎曾经给“如何成为艺术家”这个问题提供过不少答案,其中不乏在危机过后。其中一种即在“学院/美术学院/官方职业生涯”的体制下(从1816年开始):众多无论是法国本土抑或来自国外的艺术家,研习过素描、技法,聆听过教授们的指导,经历丰富(参加各种比赛,获得奖牌)。他们凭借自身的才华,借助工作室导师的提携,获得种种在法国或在国外(学成归国之后)的委托创作的机会。然而,这套体系完全不符合现代艺术,尤其是印象派出现之后的情况(1874):一边是学院派艺术家,他们掌握一定的方法、技巧、传统,可以传给年轻人;另一边是自由艺术家,他们受大胆的批评家和画商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使自己新的艺术取向获得认可,使艺术活动成为一种持续的创新,从而激励年轻人寻找自己的创作方向。
这种艺术自身的结构性革命带来的后果,直接挑战美术学院的艺术观念和教学制度。表面上,问题似乎相同:“艺术是可以教授的吗?”。但是,第一个问题追问的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天才是否需要训练和培养,或者怎样培养;而第二个问题追问的是传统艺术是不是艺术的本质和最高形式?如果不是或不完全是,那么人们要在美术学院里做什么?这个问题首先在十九世纪末欧洲的美术学院中提出,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演化为公开的讨论,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以培养自由艺术家即纯艺术家为职责的美术学院的结构与方法。越来越多的美术学院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美术学院,转向为设计学院和视觉创意学院,从科学上,特别是从技术上返还到学院的科学性方向,或者技术的训练方向,从而一次性消解了美术学院历史的二个问题和二重矛盾。
中国的美术学院自从引进西方制度之后,还存在着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希腊古典—文艺复兴艺术观念与中国的书画和“艺”的观念之间的差异。这个问题从消极的方面来看,阻碍着美术学院的精神实质在中国的传播,增加了学生用纯粹科学方法观察世界、掌握造型手段的难度;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对于上述美术学院的双重问题一开始就有一种批判,或者说有一种审视的眼光。中国传统的艺术观念,既不同于西方古典艺术观念,也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观念,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具有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学者和艺术家在学院制度引进之初,就已经考虑如何把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和传习方法羼入学院,为创造性地建设美术学院,在世界范围内作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探索。
中国的美术学院虽然是一个引进的制度,但是它又是中国古代画院制度的一种现代化的呈现,但是这次现代化进程并非画院制度自我更新的结果。在以画院制度为典型的中国的艺术传统在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之后,为了救亡图存,国人利用各种渠道、各种方法向先行发达的国家求取改造自己的国家、复兴自己民族文化的教育制度、训练手段和创作方法。从西方引入的新制度替代了画院制度之后,在中国形成并逐渐演变。但是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措施,还是保存和发展民族艺术的韬晦策略,美术学院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一经开始,无不受到这个国情和艺术传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当学院制度引进之后,一方面国人不断吸收和引进外文化的先进成果和成功经验,先后从日本、美国、西欧和苏联考察制度、派员留学、引进教师;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尝试与中国的伟大传统结合,试图让自己的文化通过制度性的教育和传承,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并且能够一木秀于林,在文化的某些焦点上发挥其特长,引领世界,从而完成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方面学习西方,一方面独立发展自己的文化,就构成了中国的美术学院建立近百年来丰富多彩、复杂深刻的历史。
纪念吴作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恰逢中央美院院庆九十周年,共同举办学术研讨,美术学院作为研究的主题正当其选。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近年来设立专项整理和研究吴作人档案,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研究吴作人任中央美院的院长时如何设计、推行美术学院的机构建设和教学活动;进而,就吴作人早年如何接受中国国内和西欧美术学院的教育,以他本人对在学院的学习经历和历史机遇形成的理解和认识为线索,逐步涉及近代西方美术学院系统引进的历史。潘公凯院长和范迪安馆长就把具体的事情委托我们工作组代劳。现在是谭平副院长负责此事,我们在做学术整理,向他汇报。我的建议是来研究美术学院的历史和美术学院目前遭遇到当代艺术的所面临的新问题。研讨会的主题拟为《美术学院的历史与问题》。因为时间和选题的限制,这次问题讨论集中于美术学院遭遇多元化艺术观念(如现当代艺术)冲击的问题研究,而不侧重学院的教学内容和体制设置等另一大类的问题。这次会议因为是配合中央美院“院长论坛”举办学术会议,所以在会程中也不涉及对学院行政和具体办学观念与办法的讨论,力图针对一种专题,积累一点学术成果。
讨论会论文主要分为“历史”主题和“问题”主题二个部分。“历史”主题是对世界历史上的美术学院的历史和中国引进学院制度及其发展进行的研究,此次研讨会约请了专家撰写美术学院历史的论文,追本求源。由于会议具有校庆和纪念的性质,其中有一部分论文选题相对集中于中央美院的历史专题。“问题”主题针对美术学院在当代遭遇的普遍问题,总结了国外美术学院上世纪具体的经验教训,提出国内美术学院目前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会议论文集》结稿在即,先印出文集稿本,供大会研讨使用,会后经过修订,加上未及收入的文稿,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学院的历史与问题——中央美术学院院庆九十周年暨纪念吴作人先生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