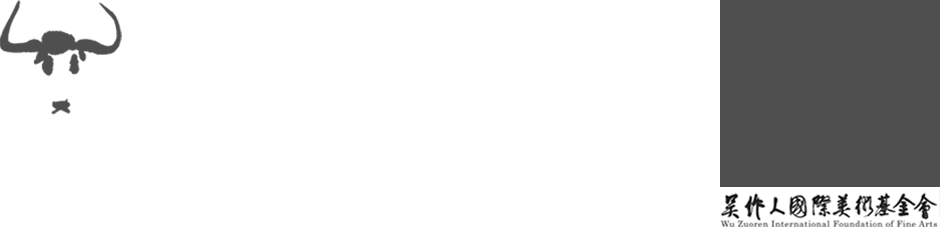简介: 照片说明:1990年11月23日晚,吴作人与阮大华在吴宅客厅“听’审读’”。 作者:阮大华 2008年11月3日,是前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
照片说明:1990年11月23日晚,吴作人与阮大华在吴宅客厅“听’审读’”。
作者:阮大华
2008年11月3日,是前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吴作人是继徐悲鸿之后中国美术界的又一领军人物,逝世已11年。屈指算来,我自初晤先生起至今已历22个春秋。时光的长镜头虽已摇远,然而先生的身影并未走远,一些昔日与他交往的珍贵场景早已凝固在我的记忆深处。随着岁月的积淀与思绪的梳理,先生的德、行、业、绩,诗、书、画、论,音、容、笑、貌,愈发清晰可感、伸手可触,我的回忆亦因之而愈加鲜活……
美协主席让行外人写评论登《名家翰墨》
1986年秋,我陪来京的青岛诗友纪宇(《刘开渠传》作者)去西单太仆寺街63号的开渠先生家做客后,因要为《中国老年》杂志撰稿,经刘先生介绍曾去吴先生处采访。而真正谈得上交流交往的,却是在4年之后。
199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应约到吴宅做客。缘由是:业内极有影响的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在其出版的国际性中国书画投资鉴赏大型杂志《名家翰墨》的第16期,拟为吴作人萧淑芳夫妇出一册“特集”,需有人写一篇全面评论吴先生作品与艺术理论的赏析性文章打头,朋友便推荐了我。
我得知此意后很是忐忑。就我而言,虽搞过一些文艺创作与评论,也研读过吴先生的作品和文章,但要我全面评论这位中国美协主席、画坛的“头牌人物”,能胜任么?就吴先生而言,业内有他众多功成名就的新老学生、有众多造诣深厚的画家理论家,为什么偏偏找一个行外人来写这么重要的文章?思考的结果是,等见过吴先生再说,看看他是怎么想的。
来到地处老虎庙花园村的吴宅,落座不久我便问他:“吴先生,我只是个记者,一不是画家,二不是史论家,三不是您的学生,怎么会让我来写文章?”
我记得,吴先生很幽默:“我先答你这个记者问,一是好画家未必能写好文章;二是美术史论家的文章,普通人未必爱看;三是我的学生虽都在美术界,但美术并不只是美术圈内的事。”
我说出了我的担心:“对美术而言我是行外人,只怕不胜任,写不好。”
“行外人不一定外行,行内人也不一定内行。”不知不觉中,“答记者问”让他变成了“问记者”,那你说,你做好记者的条件是什么?
听到吴先生平易的问话,我的回答多少有些自负:“首先得懂新闻,还要会写作–不能只会写新闻稿。我是八一年入的作协,还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中文系毕业生,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能做好记者的条件。”吴先生目光依旧那么平易谦和,继续问下去:“你画过画吗?”“小时候画过。大了没人教,又赶上了’文革’。”“小孩子爱画画是天性,长大后很多人成不了画家,有人教也成不了,我家里就是这样。”吴先生似乎拉起了家常:“插过队吧?”“插过。还陪父亲挨过斗、做过工。”“后来呢?”“回城后70年代在文化宫搞过音乐, 80年代还编过文联的文学刊物。”
吴先生笑了:“看来你不仅能对自己有信心,也能让我有信心了。我看你能写,还能写好。”
我的顾虑就在他的谈笑中打消了。临别时,吴先生在他的画册、文集上一一用遒劲而潇洒的碳笔字签上名字送我。他在一本1988年版的《吴作人》传记扉页上签完名后说:“书中有些错误出版社未校出来。我夹了个勘误表在里头,供你写作中参考吧。”
“勘误增补表”的故事
我细细读毕吴先生的传记,出版社的文字和事实错误可真不少,在一张30×10公分的“勘误表”上(看来是出版社自己打印的),竟印得密密麻麻,数数共44处。“勘误表”背面,则是吴先生手写的“勘误增补表”–他自己另外发现后、用圆珠笔记在背面纸上的三大类错误。
他写下的分类标题如下:“1.标点符号使用不当”;“2.个别错字”;“3.问题”。(其中“个别错字”部分,他列了17处;“问题”部分他以页码序次标出的列了19处,以加框文字标出的列了9处)吴先生手写的“勘误增补表”,除“标点符号使用不当”部分未逐一列出外,其余两部分的错误共45处。
特别要指出的是,他亲笔用红色墨水改在书中文内的史实、事实性错误,另外还有15处之多。如第92页:1935年9月之后由田汉操持、冼星海配乐、吴作人舞台设计的《复活》在南京上演,主演“金焰、俞珊”应为”顾梦鹤、陆露明、常任侠”。第170页,对中国第一位“首次扮演《蝴蝶夫人》女主角巧巧桑的著名女高音歌剧演唱家费曼尔”艺术生涯的介绍等处,都有事实、史实方面的硬伤。吴先生对这些错误都一一改了过来。
第345页1个页码中的错误竟多达6处。其中关于凡·高兄弟逝世、墓地的错误表述,与事实相去甚远,吴先生干脆用红墨水另外写了一段话换上去:“六个月后,兄弟相继去世,两人的遗体被同葬在巴黎近郊,AWERS-SUR-OISE的一座小公墓里”。
“勘误增补表”与改错的红墨水字虽小,却记录着吴先生治学严谨、办事认真的大家风范。它既是先生留给我的奇特纪念,也应视为吴作人研究中的珍贵史料和文物。
作画作书作诗作文,首推“作人”–对作人先生的人格解读
与大师相逢实乃幸运,相逢若能相知我认为已属幸福范畴了。幸福的涵义在于与大师相知后,获知的充实感,获教的愉悦感,以及对其人格由景仰而产生的崇高感。为完成先生的重托,同时也可使自己的学习与写作出现一个新领域新高度,我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集中收集、复读、新读了与吴作人和美术创作、研究、评论有关的十几种文献、资料,做了数万字的心得笔记,可谓获知获益多焉大焉。动笔之前,我逐渐形成了一些感觉,并归纳出若干的写作角度:
——吴作人的国画是”学者画”;其”学者画大师”有着独自定位;
——吴作人诗、书、画”各具面貌又相互彰阐”的理论贡献与个性;
——诗性、音乐性在吴作人绘画主体中的视觉体现及创作特色;
——吴作人国画中的”造境、凌境”与”题材性格”之双向吸引;
——透视、造型与气韵、语言:由油画家而国画家及其技法略述;
——画家作书与书家作画:吴作人书法技巧之于国画创作的作用反作用;
——画家作诗与诗人作画:从吴作人诗歌创作看”缘画为诗”与”缘诗为画”之关系;
……
提纲列出后,细想想,多了。贪多嚼不烂。写他可大致分为作诗、作书、作画、作文(理论)与育人等。范围太大,非一文所可及,如上7个大题中择前4个为之可集中可展开,有利于可读、耐读又不至于“掉书袋”。于是将后3个舍去,拟日后另文作学习研讨。
但是有一点决不可忽略,那就是吴作人作为一个中国画家、中国画坛领袖人物的人格与人格力量。他于1908年生于苏州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之家,1927年起先后在上海艺术大学、南国艺术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学习美术。1930年起先后留学法国巴黎和比利时布鲁塞尔,其间曾获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金质奖章和桂冠生荣誉。1935年应徐悲鸿之邀回国,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国立艺专任教授、教务长,1958年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的艺术生涯几乎等同于整个20世纪的长度。而对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更加注重其人格及其力量–
在旧、新中国,当战乱纷仍、军阀横行、民族危难、时代变迁、政治风雨、革故鼎新等“大风大浪”之中、之后,他在哪里?在做什么?做得怎样?评价如何?他的人生、作为、作品之于国家、民族、民众,作用效果如何?在上述诸种已具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高度的重大命题中,我一一找到了这位画坛伟人的闪光足迹,找到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的艺术创造佳绩与对民族、国家的杰出贡献。中国近现代画史上像他这样的大家可谓屈指可数:
——天资聪颖,历尽磨难;青年才俊,“金奖折桂”;学贯中西,出类拔萃;蜚声画坛,巨构如碑;教书育人,桃李天下;
——30年代冒死赴抗战前线写生,以画作焕发国人之志之力;40年代即不畏艰辛长期深入藏区、西北诸省采风,为民族艺术身体力行;解放前夕与徐悲鸿一起团结师生力拒北平艺专南迁,与反动势力相搏拔剑而起;
——50年代即成为新中国画坛领军人物,居功至伟;80年代分获法国政府“艺术文学最高勋章”和比利时国王“王冠级荣誉勋章”,享誉海内外。史实事实俱在,毋庸赘述。对他这位历经沧海而见本色、代表着“民族脊梁”的画坛大师,必须给予应有的立论高度。经过几个月的研析,我把“伟大的画家,嘹亮的名字”写进了文尾对先生的“结论式”论述中。
吴作人“听’审读’”:关于“镉”“铬”二字及其他
当年11月三稿改毕,润过色便联系吴先生审稿子。23日晚上7时多到的,稍事寒暄,我从大信袋中取出那篇《画、书、诗、论:吴作人国画艺术特色初探》,一万八千字,300字稿纸抄的,60多页厚厚一摞。要交作业了,不免有点不安:“吴先生,您看后有意见尽管说。”吴先生笑眯眯地道:“你怎么知道我有意见?”我说:”我水平有限。”
他说:“谁没有限?这样吧,你读,我听。听你读,算我审。出版社这道工序叫’审读’,是一个人干的,我们二人合作,叫’听审读’吧。”他转过脸对夫人萧淑芳道:“茶水伺候。”
我轻松起来,喝过了萧淑芳先生的茶又吃了她端出的点心,清清嗓子,便用中音很慢地读了起来。我担心声音低了、语速快了先生听不清楚。哪知才念了半页,他亲切地笑了,说:“’廉颇老矣,尚能听矣’。你可以再低些、快些,这样你一不会太累,二不会时间太晚。”萧先生也笑了,她坐在吴先生身边木扶手的小沙发上,边织毛衣边点头,示意我照吴先生的话办。
先生聚精会神地听,我字正腔圆地念。(见照片)我不时用眼角余光瞧瞧二位先生。我看到,一旦我念到经深思熟虑、以言简意赅的文字表述出的独自观点和感觉,吴先生微阖的双眼中,就似乎掠过些许亮光,萧先生脸上会出现更多笑意。我受到了鼓舞,愉悦不时涌过心头。
稿子念过一多半,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了,萧先生又为我续上茶水端过来:“喝点茶,休息十分钟。”我说:“不累不累。”萧先生笑笑说:“’廉颇老矣’,他会累呢。”我明白了,于是遵命,喝茶吃点心。
萧先生去弄了热毛巾递给吴先生。看来他是累了。他慢慢地、很有力地一一擦过双眼、额头、两颊与左右耳朵,把毛巾交给萧先生,对我道:“来吧!”我说:“稿子不多了,再歇歇吧!”他说:“听戏要一气听完,停久了,戏路就接不上了。”
我又开念。历时两个多钟头,近两万字的稿子终于”听审读”完了,除开篇的那次,他从未打断过我。
我刚念完文尾的“11月3日至18日再改”最后几个字,他突然问我:“你刚才念的那个’ge’字,用的是哪个字呀?是二声的’gé’还是四声的’gè’?”
我一头雾水:“什么’ge’字?”
见我不解,他慢慢道:“就是你写我画金鱼的’帽子’–写我画’红头金鱼’时的那句话。”
我明白了,往回翻到了稿子第五部分第五段中,找到了那个“ge”字,说:“是四声的’铬’字。这句话是说你用上好的’铬红’给红头金鱼着色。”
先生笑了:“不对了。这种同音字在金属元素中是两个字,两种音调,是四声’铬’与二声’镉’,代表两种元素。你用的是’铬’,而用在红颜料中的,只能是另外一个’镉’字。”他顺手拿过一支圆珠笔,在我装稿子的大信袋上,写下了拇指甲盖大的一个“镉”字给我看,并解释说:“只有这个’镉’能掺到颜料中,它会增加色的亮度。所谓’英国红、西洋红’,都加了镉。”
曾组织翻译并亲自校正审定法文中译本《罗丹艺术论》的吴先生,真不愧学界大家,仅从我的发音上便“听审”出我用的是错的“铬”而非对的“镉”!我要求说:“您得好好帮我把把关。”他道:“稿子能留下么?有两个地方我没听准,想看一看。”我说:“当然当然。”于是告辞,出门后看看表,已近夜10时了。
3天后,萧先生打电话,客客气气地让我去取稿。我路上想着:吴先生可能给改得不少。谁知到后翻完稿子才知,他仅在几个不当用词处作了标记,还另外写在了那个装稿子的大信袋上,并标出页码所在。(那个大信袋我至今仍保存着)他说:“供你参考吧。”我于是又提出要求:“您还是给改改吧!”
他笑着摇头:“不行不行。改了就不是你评吴作人,而是吴作人评吴作人了。版权是你的,我不能’篡权夺权’。”他又解释说:“我之所以要’听审读’,是想’先听为快’。你写了我什么,我想早点知道。至于怎么写,那是你的事。”
那天晚上很开心,聊了些别的什么都记不清了。但有两段话我至今忘不了:一是吴先生说,当看到我评他作品中有音乐性元素时,让他想起马思聪在40年代看了他的藏区和大西北题材的作品后,曾说想以此为题写一交响诗;二是对我写的文章,他这样说:“这是我看到的非专业人士写我的最好的评论,好就好在观点独到而又能雅俗共赏。”
按照先生意见修改的稿子复印后拿到香港,在《名家翰墨》于1991年5月1日出版的”吴作人萧淑芳特集”画册中,未动一字置于头条位置全文刊出。《名家翰墨》还译了两页的英文摘要附登在文后。
“听审读”后的一个周日晚上,我去小羊宜宾胡同到中国作协《文艺报》评论部主任孙武臣家中做客时,带去了复印稿,向这位老朋友说起了吴先生“听审读”的事和我的感动。稿子经他精心编辑后,《文艺报》于1991年4月13日在第五版,以近一个整版的篇幅作了选载。同年度的《美术向导》杂志还分4期作了连载。
在病中,拳拳心与殷殷情
1990年12月25日,也就是吴先生“听审读”后的第32天,他不幸因脑血栓住院,一代巨擘至此封笔。出院后我去探望过几次,每次都要陪他和萧先生聊聊天,但大都不敢久留,怕影响他的休养。老先生的病情与心情时好时坏,但他病中仍关心、惦念美术事业的言情,忆来仍历历在目,令我五内俱热。
1994年6月,应陕西书画研究院之邀,我去西安参加该院建院纪念活动,归来后的次日下午又去看望吴先生。此番还将视先生的健康状况办件事:该院有1300多名会员,人才济济活动众多,是西北五省区很有影响的美术机构;他们很想请身为中国美协主席的吴先生在建院八周年之际说一些鼓励的话,以壮声色。
病中的吴先生一见我,顿时很激动,握住我的手,热泪从眼中落下来。我也不禁潸然泪下。萧淑芳先生劝住了我们,让菏泽籍小阿姨照顾吴先生到阳台上去陪我聊天。这次依然还是我说,他听。我向他说起了西北之行的观感和西安美术界的活动,聊了不一会,先生情绪就好转了,他听得很是入神,不时微微点头,问情况,可谓心向往之,神遥思之。
我对他讲了该院盎然院长的愿望,希望以他的名义发一贺电,以资鼓励,他点头。我知道他听明白了,也同意了,便当场代他拟了个贺电,念给他听了又征求萧先生的意见后,于当晚以他的名义发了出去。
这次谈话虽不到两个小时,却是我与病中的先生最长的一次交谈了。我未问过他在病中是否还发过此类的贺电,但我珍记着他病中牵挂美术事业的拳拳之心与殷殷之情。
那封贺电的内容大致为:陕西书画研究院并盎然院长:欣闻贵院建院八载佳期特遥致祝贺,诚愿西北美术事业发展平顺并颂画坛诸友夏祺。吴作人。1994年6月于京西花园村。
“悼念月”前后的追忆
1997年4月初的一天,当我与萧先生通电话中,得知吴先生又病重住进医院的消息时,心中一沉,似乎有种不祥之感。先生此番能否再次焕发他那历经劫波的顽强生命力击退病魔?我在心底为他虔诚地祝福。
我到吴宅向萧先生表达了去病房的愿望。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秘书长、其婿商玉生先生告诉了我北京医院的房号,说:“你去看看吴先生吧,他已经不能和你说话了。我女儿在医院。”
我精心选购了鲜花,急匆匆赶到了病房。这是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南楼的一个单间。泪眼婆娑且面容憔悴的吴宁,在精心地守护着重病中的外公。
先生静静地仰卧在病床上,面容依旧那样平静、慈祥。他仿佛在苍苍茫茫路漫漫的艺坛高原上,跋涉得太久太久、太累太累了,静静地入睡了。我眼眶一热,俯身在他耳边轻轻唤道:“吴先生,吴先生,我看您来了……”
我觉得先生听到了。先生虽然眼睛闭着,但我知道他在以无声的静默迎候着我。我用双手先轻握住先生身体外侧的右手,继而轻轻握住他另一侧的左手。先生这双参与创造了现当代中国美术史的大手,我已握过多次,依旧那么宽厚、那么温煦。我轻抚过先生宽阔、睿智的前额。我能感到先生的双眸和眼皮在我掌心的轻抚下微微颤动。我向吴宁说了我的感觉。吴宁说在医学上这叫因脑血栓引起的”醒觉式昏迷”。我想先生对我的声音与触动,应该是有知觉有感应的……
那是个不能忘却的日子:1997年4月9日。10日中午,商玉生先生将吴先生9日晚上9时47分辞世的噩耗告知了我。新华社关于吴先生逝世的消息、遗像通稿于4月10 日下午4时57分发出。我当晚便赶到先生家中吊唁。先生遗像上的慈祥目光,又在深情地注视我了……
那年的4月,是我记忆中的“吴作人悼念月”。新华社通稿发出的当晚,中央电视台即在新闻联播中配遗像播出。次日起,悼念先生逝世的活动逐渐形成了高潮,我发表的新闻与悼念文章也形成了高潮。我在报道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1997年4月19日,吴作人逝世第十日,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在京成立。会场上,人们望着吴作人生前最后一幅作品–为我国现代音乐教育开拓者萧友梅先生逝世50周年写下的行书’艺术首先有民族性,才有世界性’,肃然起敬。十天来,一个个花篮盛满哀思,一幅幅挽联倾诉深情,送往京西花园村的华侨公寓,摆满了吴家客厅改作的小小灵堂……”
我认为自己作为记者,悼念吴先生离不开笔与文。将吴先生独到的艺术造诣、对美术事业的巨大贡献、教书育人的名师品格告知广大读者并使之发扬光大,以促进中国美术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是我的职业所在,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于是,当月中我写下了一系列新闻、评论和纪念文章:《祭吴作人》发表于《中国文化报》第1368期四版;《永恒的怀念》发表于《北京晚报》第9127期九版;《长歌当哭》发表于《经济参考报》第5426期七版……
5月28日,吴先生辞世50天之际,他的艺术馆在他的出生地苏州开馆,我又先后写下了《吴作人艺术馆藏品巡礼》、《高塔与丰碑》、《吴作人艺术馆的藏品》等述评性文章及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些稿件分别在《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23日七版、《中国文化报》8月7日四版、《中国书画报》第707期三版等媒体刊发。
“暮春迟迟,哀思漫漫”
此处做小标题的8个字,是新华社通稿《首都各界送别美术大师吴作人》的开篇二句。吴先生的遗体告别日确定在1997年4月30日,商玉生先生提前一天告知了我。
吴作人是徐悲鸿病故后,执掌中国美术界帅印的统帅性人物,自50年代起在长达30年的岁月里(”文革”不计),先后担任中央美院院长、名誉院长,中国美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在海内外影响巨大。他对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创立、发展与改革开放后的国际交流所做的建树,至少目前无人可以超越。新华社报道中对其生平、成就的评价,相比其他画家的逝世报道,必须体现出应有的高度、深度与特色。我虽是一个老记者了,对这种重要报道,也必须提前做好功课。
我于1997年4月29日深夜提前起草了稿件的评价、背景部分等内容。30日上午,八宝山数千人”向中国画坛一代巨擘吴作人作最后的告别”。王黎同志对领导人的出席名单作了订正,增加了场景描写。新华社配照片后当日下午播发。
长长的领导人名单过后,通稿中对先生作了这样的评价:“吴作人是我国杰出的人民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美术创作、研究和培育美术新人的事业,在2 0 世纪中国艺术和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以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学者风范,融会中西方艺术精华,成为本世纪不断成熟的中国油画学派独具特色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之一”。
这篇仅有1246个字的通稿,对先生的生平与职务、学习与教学、创作与影响、深入生活与艺术思想作过概括性介绍后,现场描写有这样两小段:“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葬礼进行曲》在告别室里低回。在艺术创造与美术教学的艺苑中劳作了一生的吴作人,身覆由他的夫人、知名画家萧淑芳精心绘制的梅花缎被,安卧鲜花丛中”。”前来告别的人们献上一支支米黄色的康乃馨,深深思念这位曾为人类创造了美的人”。
首都各新闻单位和京外、境外众多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广泛采用了这篇新华社通稿。仅对中央级、省级日报的统计,次日(5月1日)登出此稿的就达40多家,大多放在头版配照片刊登。《中国青年报》将此稿放在了”报眼”位置,其醒目的对联式主标题,即从通稿对现场的第二段描写中提炼而出:“献上一支康乃馨 告别大师吴作人”。
此处要说明的是:1999年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编辑、书名为《吴作人研究与追念》的纪念文集,用的是刊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新华社通稿。因版面所限该报登通稿时把倒数第二段删掉了(此举在报界已是常例),所以收在书里的那篇新华社通稿不是其全貌。现将被删掉的部分补记于此–
“吴作人的夫人萧淑芳说,吴作人生前最大的爱好就是’跑’。深入生活是他人生的重要内容。3 0 年代,他曾组织师生战地写生团到过三省六地;4 0 年代,他在战乱中到甘、青、康、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写生,曾多次死里逃生。解放后,他更加注重深入生活。吴作人生前主张:’艺术是入世的,是时代的,是能使人理解的。大众能理解者,方为不朽之作。’1 9 9 0 年1 2 月1 3 日,8 2 岁高龄的吴作人,为我国现代音乐教育奠基人萧友梅逝世5 0 周年写下了一幅笔力遒劲的行书:’艺术首先有民族性,才有世界性。’不料1 2 天后,他竟得了脑血栓。这幅书法作品成了吴作人的封笔之作,也成为他一生艺术探索的总结。”
当年在八宝山告别室,就要回新华社了,我最后久久地凝视着身着藏蓝色西装、静卧在鲜花丛中的作人先生,不禁泪泉奔涌……永别了,敬爱的先生!
您将与中国美术事业同在。您将在人们心中和美术史中永生。您像画坛上的一座巨碑,将永远地高高耸立! (作者为新华每日电讯报社党组成员、总编辑助理、高级编辑 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11/03/content_1029915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