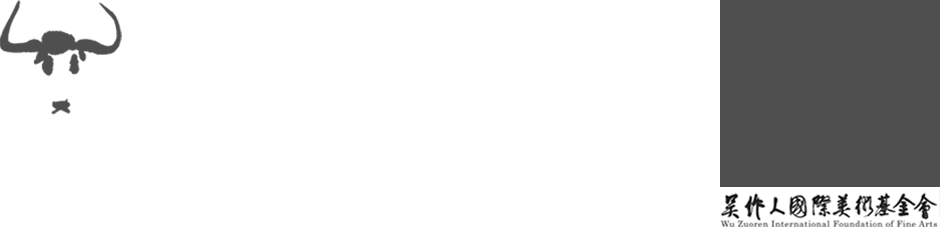吴作人
1909年出生于江苏省。1927年至1930年先后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从师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1930年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考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王家美术学院白思天院长画室学习。1946年在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务主任和油画系主任。1950年后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教学和领导工作。出版画册:《吴作人速写集》、《吴作人水墨画集》、《吴作人画选》、《吴作人、萧淑芳画选》、《吴作人艺术》等。
吴作人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正遇中央美术学院建院90周年盛典。作为中央美院的老院长,先生毕生奉献中国的艺术学院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风范犹在。因此,纪念展览特别以《学院与艺术》为题。既是借重巧合之风光,同时,的确也切近当前中国艺术的学院教育这个真实的问题。展览截取吴作人先生一生的一个侧面:从他早年入学院就学开始,留学西方,优等学成于西方美术学院,归国先后在中央大学、北平艺专,建国后一直在中央美院任教。这个经历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救国图强道路的缩影:在国家危亡关头,向西方求取真理,为振兴国家,教书育人,倾心尽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西方引进的学院制度与中国的国情和伟大传统相结合,力图开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学院,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巨作和风格。
先贤的理想和努力,在实际的施行与推动中受到特殊的历史时代的限制,或因偶然的个人际遇而难以实现。吴作人先生一人的学院与艺术的历程,也是中国百年知识分子境遇的典型,回首往事,必有感慨。而此次展览,试图把吴作人的艺术和学院教育的个案作一初步整理,初现已有分晓。虽然先生一生可谓门风浩荡,多有可以昭示艺坛之处,但实际上他的教育和创作的不少想法止于独善,屡折屡试,最终也只是留下一份资料,故本次展览又有钩沉索隐之意图。
吴作人接受学院教育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美术学院作为创造艺术和培养艺术家的场所,是西方艺术传统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概念。
艺术作为一种人文科学,不仅可以为理论所解释,而且可以通过教学传授,从而构成理性,形成权威。艺术学院一度是许多国家的艺术殿堂。然而,在西方学院传统中一直存在一股质疑的思潮:艺术是人的天赋,不能被规范、被传授。这股与学院相悖的力量改造并丰富了学院传统,使学院增加了观察自然、营造风格和创意构图的内容。19世纪中期,现代艺术的出现对学院的基本性质提出了挑战,竟将印象派风格引入学院,而印象派之中包含诸多艺术风格,其共同意向正是反对学院。20世纪初,西欧的重要艺术活动已经不必然出自学院,但是文化传统巨大的习惯力量依旧为学院保留着广大的市场。直到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学院的性质才彻底改变。在新型的艺术学院中,新一代天才受到杰出艺术家的启示和激发,进行着新的创造。
学院性质的变化反映了更为深刻的艺术观念的变化。学院制度创建于文艺复兴时期,当时新发展起来的艺术观念是一门人文科学,是由人的理性精神建立的与艺术相关的各门科学的集成,诸如透视法、解剖学、力学和材料科学,它们使艺术家可以在一个平面或空间中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幻象世界,而对这一幻象世界的评价标准是其接近物质世界真实形状的程度,就是要画得准确、画得像。在写实技术的基础上,这个世界再进一步传达和承载高贵、典雅和悲悯的精神。这是希腊—希伯莱传统的艺术观念,或可称之为西方经典艺术观念。
19世纪30年代,摄影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使得制作幻象世界愈加方便。印象派的怀疑和探索终于在后印象派中完成,艺术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艺术与现代科技具有不同的作用,艺术不必再关注外在的形象世界,而是要重视实验创新,关注人的内心和本性。这种观念直接与西方经典的写实艺术观念相对立,从而导致了学院的革命。
在西方学院与艺术激烈变革的同时,中国却处在国家存亡、文化危急的关头。知识界形成了采用西方先进科技来改造中国的思想。这种思想导致了学院制度的引入。因为这次引入针对的是中国艺术的传统方法,所以出现了主动误取的历史现象。引入者们有选择地把文艺复兴传统的写实的学院艺术引入了中国,完全或者几乎没有顾及西方学院本身的危机,以及西方艺术正在发生的重要变革。
中国的艺术学院在开创初期,亟待师资和方法,因此遴选优秀的青年留学西方就成为政府和民间共同的认识和行动,特别是对中国艺术教育的格局有想法的前辈,为此进行了战略部署和有计划的推行。吴作人就是这样一位入选者。就这样,吴作人进入了欧洲的美术学院,成为完整吸收和习得欧洲艺术学院制度和方法的中国留学生。
吴作人不负众望,在欧洲的巴黎和布鲁塞尔接受了全面完整的学院教育。因为资助的原因,吴作人从巴黎转入布鲁塞尔的皇家美术学院学习。这一次转变带来一个意外的效果。布鲁塞尔近代有“小巴黎”之称,居民主要操法语,制度风气与当时的巴黎相近,至少,在艺术学院的制度和风气上是接近的。但是,这里又不是巴黎,没有那么丰富、热闹,最重要的是布鲁塞尔不是现代艺术实验的中心,现代艺术带给艺术学院系统的重大冲突此时还未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明显地表露出来。所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师资、课程、工作室、学籍制度和评价系统更符合中国派人留学亟需引进的初衷,这里有西方经典意义上的学院制度。吴作人先生得遇良师,并且学业优秀,获得金奖,并以桂冠生的荣誉毕业。
回国之后,虽然任教学院,进修则是日常功课。吴作人坚持教学相长,终身学习。身为院长,以身作则。
下乡实际上是校外考察和写生的习称。下乡是美术学院教学的必修课,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每学年,甚至每学期都要从学院走出去,来到人民中间,来到自然中间,来到生活中间,来到艺术与社会的直接关口。深入生活,了解人生,正是下乡的含义。
写生本是学院教学的补充。吴作人从西行中,接触传统,了解西北民族和民间风情,开拓了眼界,受到了色彩和气象的激发,完成了自己艺术风格的重大转变。而写生作为毕生的功课,吴作人从未止步……
考察是个人向艺术传统和人类文明的历史遗产不断学习、继承发扬的又一门必修功课,吴作人的考察也从未间断。
吴作人的艺术教育思想以及在学院建制、基础教学、创作教学及其他教学方面的实践、成绩
1953年徐悲鸿去世,吴作人承担了从北平艺专系统沿袭下来的教学主张和教学理想,此时正遇国家要求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又遇到苏联的艺术教育体系的引入。如何提高自身的学术素养和后来被称之为“徐悲鸿学派”的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主要就体现在“十张纸斋”的个案之中(2007年专门举办了十张纸斋的展览)。与苏联教学方法的相互配合也成为当时学院建制和教学内容设置的重要方面。在这次展览中用各种文件和手稿做了揭示。
1959年中央美术学院第二次推进业务提高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工作室。由于摄影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欧洲已经进入现代艺术时期,马蒂斯在1910年已经担任沙龙评委,毕加索一战前后已为公认,凡高、塞尚以及之前的印象派已经成为主流大师。此时的西欧美术学院在教学中已经放弃了几个世纪以来为培养学生创作多人物、大场面作品而传授的严谨细密的写实技术和大场面营造技巧,转而要求学生要在作品中体现个性和情趣,这通过吴作人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获奖作品《男人体》就可以看出,他为欧洲人所承认的不是类似大卫、德拉克罗瓦到库尔贝的巨幅油画,更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绘画和训练方法形成的古老画法,而是其具有写意概括的充满意味的作品。而俄罗斯在18世纪将这种严谨细密的教学法学到手之后,一直延续下来,又因20世纪早期共产党的提倡,这一写实技术在政治的需要下不断获得巩固与强化。因此,契斯恰科夫的素描要求与徐、吴之间是存在着不同的审美取向和学术诉求的。然而,这种不同却又因为“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法”在1950年代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的片面化(变成了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一种显影式的无休止地细描细抠)而被扩大化,从而与徐吴美学系统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又因为政治上的强势(即学习苏联的国策以及认为苏联艺术属于无产阶级的进步的艺术、西欧艺术属于资产阶级的落后的艺术的价值取向),造成了美院在基础教学上极其不均衡的发展态势。这种分歧最终通过1959年油画系三个专家工作室的建立获得了部分的解决。
工作室建立之后,吴作人的教学主张得以落实推行。
比如,吴作人关于素描“长期作业”的看法与徐悲鸿基本一致。“徐悲鸿的教学体系基本上和契斯恰科夫同属于意大利和法国的传统,有比较科学的方法,但在造型的共同原则和规律之下,他在运用上则比较更有灵活性。解放以后,我们曾有一段时间学习俄罗斯契斯恰科夫的素描教学法,这个教学体系也是和西欧传统有着直接渊源的;在造型的原理、原则上,无论是法国的,意大利的、俄罗斯的,都有许多共同点。徐悲鸿的素描教学体系和契斯恰科夫的素描教学体系,在原则上也是基本一致的。”(引自艾中信《徐悲鸿研究》)“在油画教学上,徐先生不太限制颜色,吴先生限制颜色,感觉还是北欧弗拉芒学派和19世纪德拉克洛瓦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吴先生要求色彩要非常微妙、丰富,但是颜色的丰富不在调色板上有多少颜色,不是说你什么颜色都挤上去的。他给我们举例子,好的厨师,佐料还是那些佐料,没有什么特别的,关键还是在技术、火候。他大概就是七八种颜色,土黄、土红、赭石、熟褐、翠绿、朱标、群青,然后要是有一点深红,也可以派上,其他的颜色一般不用。尤其是橘黄、橘红,他说这是要命的颜色,因为他的调子比较暖,橘黄加上去就跟着了火似的,这不行,伦勃朗的画里面就没有橘黄。吴作人和徐悲鸿讲的要求一样,但是方法不一样。徐先生就是摆,这一笔摆上去,那一笔摆上去,颜色在摆、在换。吴先生是接,是一种很随意、很洒脱的感觉,不是很吃力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和中国水墨画很相近,这样就是把北欧的风格和技巧与中国的笔墨结合起来了。”(引自靳之林访谈)
吴作人深谙美术学院作为学术创作机构和教学机构之本质,为了养成大艺术家,他把教学扩展到了修养的广阔范围。他本人首先身体力行。正如艾中信《〈吴作人作品集〉序》中所说:“早年的家庭教育,使得吴作人深受古文学、经史之学的熏陶,熟读《诗经》、《离骚》、唐宋诗词,旁及诸子百家的学说,当时虽未必通晓,学习不辍,乃奠定下深厚的文化基础,及长,便时隐时现地融会贯通在艺术创作之中。儒家的务实精神和道家的空灵逸气,相左相右,道乎中庸,造就他在水墨画上善寓教化于清雅的抒情寓意,且时有哲理性的阐发。热中美术者往往与自然科学无缘,而吴作人却对天文、地理乃至原子能都有很大的兴趣。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兼容美术和工程的建筑师,当然也是很出色的。就与科学结缘这一点说,他似乎可以追随文艺复兴大师达文西。……就文艺领域而言,除了精于诗词,又博通昆曲,特长擪笛,又偏爱苏州弹词。这些高层知识界和平民界的雅和俗的传统文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艺术气质。他的诗词清幽沁胸,发人深思。擪笛抑扬,顿挫激昂,潇洒放逸的情愫,在他的许多水墨画上化为可视的无声奏鸣。”
幸庆吴作人先生本人及其家属有心,将这段时期很多资料保存至今,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文化大革命,虽已是劫后之余烬,但仍可以勾勒出当时的西方学院的教学模式,也能看出中国一代先师是带着怎样的一种心绪和态度去学习西方,引进学院制度。虽然处于历史激变的关头,取舍在各位先辈之间相差很大,但是,一斑窥豹,虽是一人之经历,实际也是一代之精神。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11月12日